
“我們上大一的時候,最初是在學校的二手書店里買師哥師姐用過的教材,當時不只因為二手書便宜,更重要的是這些書上有師哥師姐上課時劃的重點,可是因為數量有限,后來許多同學就把教材給復印了。再后來,校園的復印店就有各年級的教材電子版了,想要什么有什么,大家也就開始用復印教材了。”日前,某財經大學兩位大四的學生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采訪時談道。
記者曾先后走訪了北京的多所大專院校,驚奇地發現現在學生們使用復印教材早已常態化,很多班級干脆由班長牽頭統一去復印店購買復印教材。更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位教知識產權的教授告訴記者,在上課時發現,自己編寫的教材,學生們用的竟然全部是復印教材,于是他直接把這件事當案例講給了學生。在走訪中,記者經過與多位同學聊天,得知其實在他們心里隱約也覺得這種做法不是太好,但因為大家都這樣做,所以也就沒多想。
復印教材不屬于合理使用范圍
那么究竟復印店未經授權擅自為學生提供整本的復印教材,這種行為是否涉及侵犯教材的作者和出版者的著作權呢?復印教材的行為是否屬于合理使用范圍呢?
中國版權保護中心副主任索來軍告訴記者,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作者通常享有復制權、發行權、信息網絡傳播權等一系列權利。所謂復制權,是指以印刷、復印、拓印、錄音、錄像、翻錄、翻拍等方式將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權利,而發行權是指以出售或者贈與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復制件的權利。在傳統的媒介形式中,對文字作者來說,以印刷的形式復制和發行作品通常是最普遍的方式,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圖書出版。此外,我國《著作權法》對圖書出版者也規定了專門的保護,就是圖書出版者對著作權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的約定享有專有出版權,他人不得出版該作品。因此未經授權擅自復印并銷售著作權人已經出版的作品,則構成對著作權人復制權和發行權的侵害,同時也構成侵犯出版社的專有出版權。
對此,社會上有些人認為復印店又不是出版社,復印和銷售復印件的行為不構成對作品的使用;也有人認為復印已經出版的圖書是為了提供給學生個人使用,因此不構成侵權。這些想法在索來軍看來都是對《著作權法》的誤讀和誤解。“對于個人使用,《著作權法》確實有對著作權人行使權利限制的規定,例如,《著作權法》規定,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這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說的個人使用或者合理使用。”他進一步解釋說。據索來軍分析,所謂個人使用通常應理解為,在使用目的上為個人自己使用,不能提供給他人使用;在使用數量上應當是少量的,應控制在自己使用的合理范圍;在使用性質上應當不具有公開性,更不能帶有商業性。以復印教材來說,如果學生自己使用自己的復印機或者借用他人的復印機對作品少量復印,而且復印的教材僅限于自己使用,應該屬于合理使用范圍。但對于公開對外營業的復印店來說,復印教材既不是為了自己使用,還有償提供給他人,顯然不屬于個人使用或者合理使用,無疑構成對著作權人和圖書出版社的侵權。判斷一種行為是否侵權,有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看它是否妨礙了作品的正常使用。書店有正式出版的圖書供消費者購買,而復印店卻擅自復印教材并提供給他人在客觀上造成出版社出版的圖書銷量減少,使得著作權人和出版單位的應得收益受到損失,顯然是對權利人的侵害。
擅自在線有償提供教材同樣侵權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現在有一種普遍現象,很多校園周邊復印店會將其所在學校各系各專業教材的電子版存儲于電腦或云盤里,只有當學生們去索取時才會進行交易,屬于按需復印。對此,索來軍認為,將已經出版的圖書內容進行數字化存儲并隨時按需有償打印,同樣構成對作品的非法復制和發行,同樣構成對著作權人和圖書出版者的侵權。
隨著網絡的發展,現在復印行業還出現了“互聯網+”的形式。也就是在自己開設的網站里將多所高校不同校區的校園復印店資源進行整合,然后向注冊用戶(以學生為主)線上提交文檔,通過線上支付平臺就近推薦復印店來撮合交易,最后再由復印店送貨上門。對于這樣的服務形式,索來軍認為,網站未經授權擅自存儲已經出版的圖書內容,通過互聯網在線有償提供給他人,同樣超出了《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范圍,首先妨礙了著作權人權利行使,構成對著作權人的侵權;如果圖書出版者取得了著作權人以信息網絡傳播使用作品的專有權,那么,這種行為也應當構成對圖書出版者信息網絡傳播專有權的侵害。
國外根本不可能復印整本教材
現在只要有點兒事,很多人就會拿國外說事,好吧,那我們就一起看看國外法律對復印這件事兒是怎么規定的。
武漢大學知識產權高級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清告訴記者,在國外,復印整本教材基本不可能。在美國就有一個判例,是某學校附近的復印店,將教材摘錄復印后匯編成課堂教學講義而被法院判決侵權。而且在國外很多大學圖書館內設置的復印機,都必須要有“不得大量復制所借閱圖書”的提示,否則,一旦發生訴訟有可能被判幫助侵權。在澳大利亞間接侵權也叫“授權侵權”,曾有大學圖書館就發生過類似的案件,最終,法院判決涉案的大學圖書館構成授權侵權。也就是在該案后,澳大利亞版權法新增第39A條,規定圖書館只要按照規定的形式給予“通知”,就可免除間接侵權責任。
總之,許多國家因為《著作權法》保護作者及權利持有人的復制權,所以未經許可且不屬于合理使用的復制均構成侵權。“在國外沒人敢整本地復印圖書,我女兒在國外讀書,她要么買教材,要么去圖書館借教材。”王清補充道。
完善《著作權法》尋求法律保護
針對目前普遍存在復印教材的各種侵權現象,索來軍認為,盡快完善《著作權法》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他提出,目前《著作權法》有關個人使用作品的規定是在復印設備不太普及,功能比較單一,復制成本比較高的情況下制定的。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復印設備越來越普及,功能也越來越多,復制成本則越來越低,因此個人使用也變得越來越方便,這對圖書出版業的沖擊越來越大。許多發達國家在多年前就已經立法,通過對復印設備(也包括對空白磁帶)征收著作權使用費,來補償著作權人和出版者的損失。
隨著數字網絡技術的出現和發展,新的存儲媒介不斷出現和更新,復制存儲和傳輸變得越來越方便,不僅進一步方便了個人使用,而且作品的個人使用和公開使用界限越來越模糊。可以說,在數字網絡環境下,如何定義個人使用,劃定個人使用的邊界,是各國著作權立法普遍需要面對的難題。“我認為,應當利用目前第三次《著作權法》修訂的契機,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并根據具體情況對《著作權法》進行適當的修訂。”索來軍強調說。
■相關案例
高等教育出版社訴某打字復印社侵害出版者權案
2015年12月28日,高等教育出版社訴吉林省長春市凈月經濟開發區某打字復印社侵害出版者權糾紛案宣判。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侵犯原告對涉案作品享有的專有出版權,判決被告停止復制、發行涉案圖書,賠償原告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1萬元。
【案情回顧】
原告訴稱,高教社享有《經濟數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的專有出版權。被告某打字復印社作為一家大型復印社,未經許可,擅自復印、發行《經濟數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影印版圖書。高教社認為,被告不僅嚴重侵害了原告對涉案圖書享有的專有出版權,而且使原告出版的正版教材銷售量減少,給原告造成了經濟損失,也擾亂了正常的出版物發行秩序。原告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復制、發行涉案圖書,被告賠償原告因擅自復制、發行該書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人民幣1萬元,被告承擔案件訴訟費用。
被告辯稱:答辯人不存在原告訴稱的復制、發行行為,原告要求被告經濟賠償沒有法律依據。
【法院判決】
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以打印方式制作《經濟數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影印版圖書系對涉案作品的復制行為,以出售方式向公眾提供該書的復制件系對涉案作品的發行行為。故法院認為,被告復制、發行涉案圖書的行為屬于對該書的出版行為,侵犯了原告對涉案作品享有的專有出版權。
據此,法院作出上述判決。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訴某圖文社侵害出版者權案
2015年12月30日,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訴吉林省長春市凈月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某圖文社侵害出版者權糾紛案宣判。吉林省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被告侵犯原告對涉案作品享有的專有出版權,判決被告停止復制、發行涉案圖書,賠償原告經濟損失7000元。
【案情回顧】
原告訴稱,外研社對《新視野大學英語》系列教材享有專有出版權。被告某圖文社作為一家中等規模復印社,未經許可,擅自復印、發行涉案圖書的影印版圖書。被告行為不僅嚴重侵害了原告對涉案圖書享有的專有出版權,且使原告出版的正版教材銷量減少,給原告造成了經濟損失,也擾亂了正常的出版物發行秩序。故訴至法院,請求判令,被告停止復制、發行涉案圖書,賠償原告因擅自復制、發行該書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及合理支出人民幣1萬元。
被告辯稱:未對涉案教材進行大量復制、發行,且沒有侵犯和對原告造成任何經濟損失;被告行為符合合理使用制度的實質條件,故未侵犯原告復制權和發行權;該復印社開業僅14個月,地理位置較為偏僻,以照證件照為主,面積較小且由夫妻經營,沒有從業人員,收入有限。
【法院判決】
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享有涉案作品的專有出版權。被告以打印方式制作《新視野大學英語讀寫教程3》(第二版)影印版圖書系對涉案作品的復制,以出售方式向公眾提供該書的復制件系對涉案作品的發行行為,被告復制、發行涉案圖書的行為系對該書的出版行為,侵犯了原告對涉案作品享有的專有出版權。
據此,法院作出上述判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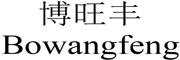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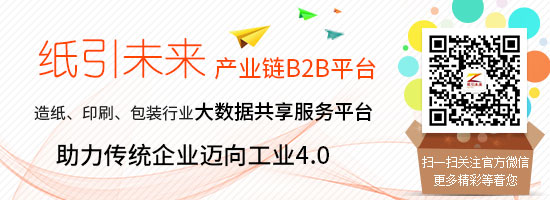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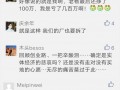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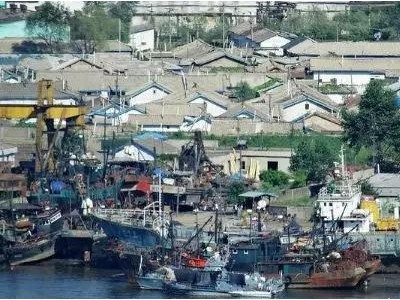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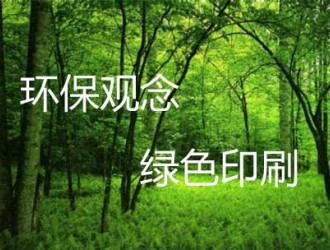


 紙友
紙友
 行情
行情
 訂單
訂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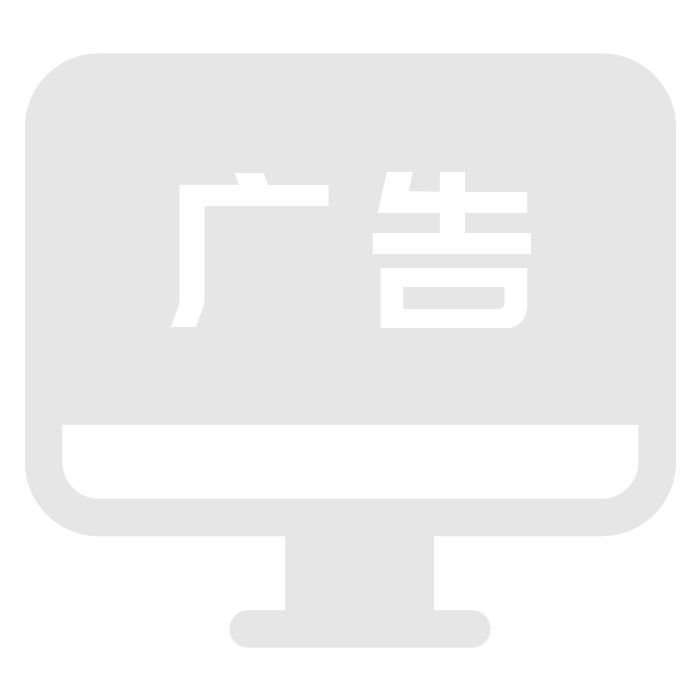 廣告
廣告
 找貨
找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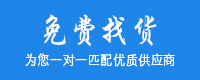
 簽到
簽到

 關注
關注
 客服
客服 TOP
TOP

